最新訊息:劃破黑暗的火種_紀國鐘老師專訪
次閱讀
時間:2024.01.18
地點: 成功大學_成大會館
參與人員:許進恭教授
文字稿作者:許進恭教授、許晉瑋教授
校閱:苗迦南
前言:
白光發光二極體(light-emitting diode; LED)已經從90年代實驗室黑暗中微弱的藍光,轉變為現在家家戶戶照明用的工具,並且也已經逐漸將傳統的燈泡和日光燈管完全取代掉。和所有的光電半導體元件一樣,高品質的半導體材料為發光二極體高性能表現的基石,若不能將高品質的光電半導體材料大規模的量產,發光二極體永遠也不會從實驗室中的工匠精品變成超級市場中人人唾手可得的日常生活用品。
在最早的III-V族半導體材料成長過程(1960 年代),科學家一開始是使用液相磊晶機台(Liquid-Phase Epitaxy (LPE)),然而此種方法就如同液相的化學反應需要不同的化學反應槽,這使得LPE磊晶過程很繁複,不利於大量生產。使用氣相磊晶(Vapor-Phase Epitaxy)或是metal-organic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MOCVD) 的機台為克服LPE問題的有效解決方案,其也是後來光電半導體技術邁向量產的重要環節。台灣在這場驚心動魄的光電半導體革命中自然沒有缺席,而紀國鐘教授在其中扮演了關鍵性角色。
在90年代初期,台灣的民主化剛萌芽,隨著黑名單解禁,一群懷抱著理想與熱情在美國已經功成名就的學者、教授紛紛回台要讓台灣民主化的嫩芽成長茁壯,紀教授就是其中一位。返國前他已經是在美國貝爾實驗室工作的知名學者,在光纖通信用累增崩潰二極體(Avalanche Photodetector)的技術開發方面有著卓越貢獻。在90年代返國後,隨即進入工研院服務,其領導的技術團隊首度將MOCVD 技術和機台導入台灣,並成功長出高品質的AlGaInP紅、黃光LED磊晶片。這些磊晶片也成功供應了國內第一家LED公司(國聯光電),使其可以順利量產高性能紅、黃光LED晶粒。這些開創性的貢獻也讓紀教授領導的技術團隊後來從工研院spin off,成立了台灣規模最大的發光二極體公司(晶元光電,Epistar), 這間公司後來成功讓白光二極體大量生產,讓台灣的LED產業可以和世界大廠競爭,並享受到該產業起飛成長時的高獲利。
紀教授從工研院離開後,隨即加入中央大學物理系。除了繼續在學界戮力於開發氮化鎵的LED技術,他也懷抱著熱情入世的精神,在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時加入了民進黨政府。他在2000年之後於研考會服務期間,成功將電子公文系統在政府內建立。這後來也如同星火燎原般,使得全國各級地方政府和大專院校普及採用。
紀教授在科技和政治界的貢獻就如同普羅米修斯的火種般不僅點燃了台灣整個LED產業輝煌的年代,也在台灣人追求民主化的道路上點燃了一盞明燈,帶來了希望和勇氣。在這期專訪我們很高興採訪到紀教授,聽他分享他波瀾壯闊的精采人生故事。
Q1.今天很榮幸能夠採訪紀國鐘老師,可以先請紀老師簡單介紹一下自己的故鄉、成長背景與童年回憶嗎?
我是出生在鳳山,但是我的父親及祖先都是臺南人。我記得有一次我父親帶我去掃墓,他指著墓碑說這個是第13代的開基祖。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不定我們家族在臺南已經超過200年了, 是道道地地的臺灣人。 我在鳳山讀鳳山國小,再去讀高雄中學。這裡面有一點小故事,就是我考初中的時候 (現在的國中,那時候叫初中) ,高雄中學在那一年變成示範學校,就是因為他是省立高中,變成只收高中生,不收初中生,所以我就離鄉背井去考屏東中學的初中部。在屏東中學的初中部讀完一年級的時候,高雄中學有初中部的留級生級,留級生人數沒有到達成班人數,所以就收插班生補足該班級人數,我參加插班考試到高雄中學初中部就讀二年級。在高雄中學,最值得記憶是,因為初二就只有兩班,而我喜歡踢足球,就參加足球隊變成足球校隊。在足球校隊裡就開始碰到很多不一樣的人,比如說留級生,他們不是說腦筋不好,就是很喜歡玩,所以我就學到很多,包括學到很多好學生不會去做的事物,但是自己還是一心一意想要把成績讀好,所以通常都是拿著一個書本,然後在操場旁邊的樹下讀,如果足球隊練球時我就會過去,跟他們踢足球。踢足球後回家,我媽媽就會說,你今天又踢足球了,我通常都說沒有啊,我有在讀書啊。但他一聞我的衣服有汗味就知道我有沒有去踢球了,沒辦法狡辯。這個大概是我讀中學的時候比較有印象的事情了。說到故鄉,當然就是鳳山。在我們年紀還小的時候也不曉得鳳山的歷史,其實在清帝國的時候,鳳山市是比高雄還要來的繁榮,可是我們小時候要看一個電影都要去高雄。
Q2.可以請紀老師分享自己求學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課程或是老師嗎?求學生涯中有什麼有趣的故事? 而又在什麼機緣下,使紀老師決定走上科學和工程這條路呢?
初中、高中畢業後,參加大學聯考,其實我並不是一開始就讀臺灣師範大學。第一次考大學是考到成大工商管理系,事實上我一心一意想要讀物理系,那時候工商管理系是屬理科學系,所以我才會填到那個組,這個組有物理,也有微積分的課程,理組的科目包含很多,當然多讀了一些經濟學相關的科目,讀了一年之后,我本來想要轉到成大物理系,但是我看我的好朋友們都在臺北,我沒有去過臺北,很想去臺北看看。
所以我自己準備了一個月,然後就再去考一次大學聯考,結果考一樣的分數。 但這次我填志願的時候就選台大跟台師大,結果錄取台師大物理系。 讀師大有一個好處,就是不需要學費,因為是公費生,連住宿舍也是免費,還給你三百塊台幣吃飯的錢,不過那是飯票,是每15天給一張。學校餐廳內的伙食吃久了,我就覺得吃膩了,所以我就跟很多人一樣,把一部分的飯票賣給別人,那誰在買呢? 工人,因為外面的工人他們沒有太多錢,所以他們就買這些飯票到學校來吃飯。我們就用當家教賺額外的錢,到外面的自助餐吃稍微好一點。
說到在台師大讀物理還蠻有趣的,因為除了大一物理之外,或者是電磁學都讓我大開眼界,為什麼?因為那時候有柏克萊大學的一套普通物理的書,分成4本,記得是力學一本,然後電磁學一本,好像熱力學及光學各一本的樣子,這幾本書整理得非常好,我的大一普物,就是靠這幾本書。我在大一的物理成績很好,我自己也很有信心,以後一定可以當個物理學家,說不定還可以拿諾貝爾獎。 可是到大二的時候就發現說,這個有一點不現實,為什麼?因為我們的老師是號稱北大畢業,但教到一些比較近代的主題,就教不下去了,我們當學生的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就他在上課得時候讀柏克萊那套書的電磁學並做筆記。 但我們這位教電磁學的教授要我們大家抄他上課的筆記,然後學期末就交筆記本作為評分的一部分,我也交了筆記,不過是讀柏克萊那套書的筆記,跟他講的完全沒有關係,我還真大膽到沒有去抄別人的筆記交差,是用我自己整理的那本筆記,還有彩色標記的哦,交給老師。結果學期成績只有78分。事實上,這個教授看了我的筆記本,本來要把我當掉,是我們物理課的助教幫我講話,助教說這個學生成績都很好,每一次考試都有80幾分以上,不要把他當掉。所以那個教授說可以不當掉但不能給他80分,只給我78分了。然後第2個更妙的故事是大三下學期,開始讀量子力學。 開課的老師是我們系裡面少數出國留學的老師,是留學日本碩士畢業的老師,他來開這門量子力學或是量子物理的課,他是一個臺灣人,他很誠實的說,我從來沒有讀過量子力學,但是我找了這本原文書,我們一起讀,那一本書是一個蘇聯的物理學家寫的,真的很棒的物理學家。 可是那一本書是俄文翻成英文的,所以很難讀,書裡面有習題還有例題,例題都有提示要如何解題,但大部分的習題,我們都不會解,老師也不會解,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想說,這跟諾貝爾獎好像越離越遠,心裡想說,好吧!那就好好做一個物理學家,好好把學術基礎紮好,以後的事就再說吧! 所以我在大學階段的課業方面,比較有印象的部分,大概就是這樣子。跟現在的大學生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資源很少要靠自己摸索,值得一提的是,那時候我知道我在臺大的好朋友們,他們是幾個人一起讀書互相討論,但是我在師大而且從南部上去的學生也沒什麼朋友,少有人一起讀書研究功課的,因為讀師大的大部分人可能想說畢業了就去當中學老師,沒有需要說什麼都懂,就把高中物理,國中物理讀懂就可以了。
所以我都一直鼓勵學生在讀書或研究實驗方面要跟同學討論,然後不懂的地方,兩三個人討論一下可能就會懂,那時候沒有用這個方法,所以大學四年也就這樣過去了,不過成績都很好。生活方面跟初中高中很像,還是一直踢足球,我還當了3年的系隊隊長,本來是大三才可以當隊長,結果我大二的時候就當隊長了,因為大三學長有2個人競爭當隊長,擺不平,就找我當隊長,因為這是大部分隊員可以接受的方案,那也是民意啦。雖然我這個隊長大三、大四的學長不太理我,不過我都很認真地參加集訓踢球,因此大三我就繼續當隊長,到了大四又一樣大三的隊員又擺不平,結果我又被推出來繼續當隊長,所以我當了3年的隊長,是很特別的經驗。當隊長讓我學習到一點就是說你一定要把人家不要做的事情撿起來做,你才是隊長啊。比如說大家搶著要當前鋒或後衛某一個地方,又或者是中鋒,左邊右邊沒有人要的,那就是隊長來做,所以我成為全方位的隊員。因此在足球隊裡也讓我學到說,其實為什麼人家會要你當隊長? 就是你要有服務及以團隊成敗為核心價值的心態,不是你要搶著功勞,或者是你要搶著當成進球的明星,你球可以傳出去讓你的隊友進球,目標就是要贏得比賽。這過程讓我學到很多的處事原則,像是後來我在大學教書的時候,獲得大計畫任總主持人,我絕對不是拿最多錢的一個分項計畫,也就是說我要一個團隊強,不是隊長強,而是大家都很強才可達到真正的成功。
大學畢業後,我們師大畢業生是要實習一年,大部分都派到國、高中實習。我的成績都在班上前幾名,所以我被留下來當助教,話說那時候已經開始有我們的校友出國留學,拿到碩博士回來當老師的,所以那時候師資已經比較好,那些博士學長回來,看起來就不一樣了,他們就有一些想要做研究工作,我們大部分的老師們都只是純教書沒有做研究工作,因此實驗室都是我們這些助教在管理那些購自國外的實驗儀器,譬如說雲霧室(cloudchamber)。那這些都是德國公司做給大學或者是高中用的實驗設備,可是負責這些設備的老師們不會用,所以我想到這個我就覺得很好笑,我靠雲霧室這個實驗所獲得的經驗,去申請耶魯大學的時候,與教授評量時,他們覺得這個人對雲霧室相關知識都懂,還會自己組裝X Ray,然後量測晶體結構,雖然這些都只是基礎的實驗性工作,比不上前瞻研究所用的設備。但當初我GRE及托福都考得不錯,所以耶魯就接受我的申請,我覺得我那時候申請到耶魯的博士班,可能我在當助教時在實驗室所學到的相關知識有加分。但是進去耶魯以後真正是大開眼界,光是螢幕顯示器是一整排,所用的雲霧室也是如一間教室那麼大,全部都電腦控制,而擁有那些設備的教授是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實驗室裡很多學生勤奮的工作,看起來都非常專業的樣子,我就像剛進校園的小學生一樣,充滿好奇心並開始我的博士班研究工作。
我到美國留學本來是想要研究核子物理,可是那個時候耶魯的加速器當機,已經超過兩年還沒修好,所以前面的博士生都沒有辦法做實驗,導致畢業都延期,我想說如果我選擇研究核子物理,可能會讀很多年才能畢業,所以我就趕快轉到固態物理領域。我是在應用科學系讀博士班,應用科學系其實是一個學院,包含固態物理,材料,還有電機等研究領域。我們那時候讀博士班做研究就是十八般武藝都要會,包含機臺的修理,軟體都自己寫來分析實驗數據,所以其實我們這一代台灣學生是比較困難的,為什麼?因為我們去讀書的時候,我們什麼先進的實驗設備都沒有摸過,所以一開始在耶魯作研究的時候,都靠同組的美國同學幫忙,美國同學在那邊做,然後我就認真學, 我學到非常多實驗知識及技巧,美國同學真的非常厲害,這就是第一年的震撼,所以我是覺得說美國的教育其實還是比我們那年代的教育水準高太多了,但現在臺灣的教育已經好很多了,差距沒有太多。有些家長會問我說,這個我小孩子沒有考取臺大、交大或成大,去讀中字輩的學校好嗎?是不是讓他重考呢?我告訴他們,如果你的小孩並非有常高的資質,其實沒有必要重考,現在台灣前段班的國立大學的老師,大部分都是畢業於一流學校的博士,你的小孩子,如果能夠學到他們的真本領啊,那已經了不起了喔。所以我相信哪一個學校沒有什麼差別。如果他真的想要更進一步讀研究所,就可以考慮到台清交成讀研究所,或者是甚至到美國一些頂尖的學校。 總之,臺灣的進步真的很多,尤其是在大學。我現在退休了,比較有機會跟社會上非理工或者是跟大學比較沒有關係的人,例如企業界的老闆也好,或者是政治人物,我都跟他們講說,其實臺灣這幾年的進步是因為我們的大學教育,除了已經培養一些研究做的很好的教授,有些現在都已經是國際級的,然後他們也教育出優秀的學生成為我台灣科技業的堅強主力,造就現在令世界各國羨慕的資通訊產業生態,所以臺灣真的是已經走上一條成功的路了,這就是我認為我們的大學教育是成功的。
Q3.請問紀老師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為何?有什麼有趣的故事嗎?而又在什麼機緣下,讓您決定走上光電半導體研究這條路呢?
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實有點戲劇性。我念博士班時當然是希望趕快畢業,然後能夠趕上我的同學,結果我真的做到了,我在耶魯3年半的時候,我的老師就要我畢業,那時候我有點沒信心,想說我的學長們都五六年才畢業,那我3年半畢業,而且英文也不怎麼好,所以我說我讀4年,但我想說先回臺灣找工作好了,然後回去再把論文寫完接著畢業,因為要到回臺灣的大學教書也要一段時間進行聘任程序,我的老師也很慷慨說,你寒假就回臺灣看看。我回台灣就安排了到大學裡演講,譬如說師大及清大,也到中鋼,因為那時候有朋友介紹我去演講,結果中鋼很快的就說要聘任我,我記得我跟負責的主管說,我不是研究金屬材料的,我是研究物理材料或者是半導體方面的東西,他說沒問題啊,只要有博士學位,我就聘你,但我沒有馬上答應。 到清大演講的記憶是,演講會後大家在喝茶聊天時,有一個學長拿到博士學位回清大教書已經了3年了,他就問我說你想要到清大來教書嗎?我說如果有機會當然很好。他說,我勸你不要回來,我說為什麼呢?他說他回來3年了,他拿不到研究經費,那時候研究經費不是跟國科會申請,是政府把經費給大學,再由學校分配,他說他去跟校長講,他需要一些研究經費設立他的低溫物理實驗室,但校長給他的答覆讓他嚇到了,校長說我給你這麼多薪水了,我沒有錢可以給你做研究了,這段話我也很驚訝,為什麼?清大那時候是台灣擁有最多經費的學校之一,雖然給的薪水比較多,但是研究經費就很有限,所以其它學校可能更困難了,所以我一聽說校長講這種話,我也很驚訝。其實這也不太對呀,在大學裡你拿薪水,不是只有教書還要做研究啊,特別像清華大學這種學校,如果只教書,薪水應該只拿一半才對。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文化或者是學術環境不大對。
剛好那時候我的指導教授從美國寫了一封郵簡,那時候不是用正式的信件,大部分都是郵簡,就只有一頁,郵費最便宜。我想說我再2個禮拜就要回美國了,為什麼還要寄信給我呢,我打開一看,原來是我的老師說他已經幫我送出20封求職信,然後我回美國會有一些interview。 那我那時候也不是很想要留在美國,那我也沒有想移民,話說那時候我們讀研究所畢業後馬上可以申請移民,我沒有申請。我想回台灣工作,結果他寫那封信,所以我就想說回去美國之后去試試看再說。就這件事我後來有想過,美國這個國家為什麼會興盛,就是像我老師這種人,他認為我這個學生很優秀,認真工作且腦袋也不錯,又很誠實,會的就講會,不會就講不會,所以他認為這個學生應該要留在美國貢獻所學,而且付諸行動幫忙找工作。因為我回臺灣找工作,他怕我答應人家,所以他才寫那封信,我也很感動他的用心,所以我就回去美國之後就去了一些單位interview了,有IBM、Bell Lab 及一些大學請我去演講。IBM有給我offer,還有另外一個學校也給我offer, 不過我後來選擇到貝爾實驗室(Bell Lab),講到Bell Lab那一段期間,我覺得讓我印象最深刻之一的事情,就是一些年紀已經很大了,60幾歲甚至70幾歲的研究人員,他們一生的研究都在貝爾實驗室,沒有在其他地方工作過,他們有的非常的開放,所以都常有大學教授來跟他們合作,他們很多也出去跟國際上的研究人員合作。我剛進去不久,就有很多年紀大且資深的研究人員來跟我聊他們的研究並合作一些研究主題,平常大家也蠻合得來的,可是有時候你在走廊或者其他公共空間遇到他,跟他打招呼他竟然看都沒有看你一眼就走過去,可是過幾天後遇到他,他卻又熱絡的跟你談論起研究的東西,我的解讀是他們是把研究的工作做到廢寢忘食的地步,非常專注,進入到幾乎忘我的程度。
我在貝爾實驗室工作期間主要是研製光纖通訊用的LED、PIN,雷射二極體及雪崩光偵測器(Avalanche photodetector),由於貝爾實驗室當年是世界上最頂尖的研究單位,研究人員所做的研究主題都是各領域最前瞻的,因此目前許多主導科技進展的發明也都始於貝爾實驗室,我在雪崩光偵測器的創新研究方面,主要是開先例使用離子佈植技術避免edge effect以提升元件的性能,在這期間,我也因為一些不錯的研究成果獲得了貝爾實驗室傑出貢獻獎。
Q4.為什麼為想到回台灣工作?
我從博士班畢業進入貝爾實驗室工作總共13年多,參與或主導過很多新的技術的開發也獲得了不錯的成果,工作內容主要是技術開發方面。我想說我應該在管理方面可以有一些發揮,剛好1990年的時候,李登輝已經擔任總統了,那時候的臺灣政治氛圍,對我們這一些在海外經常參與臺灣人同鄉會活動的人,已經比較不會敏感了。此外,我父親剛過世兩年,我想趁母親還在,我也該回來台灣了,這個是我第一個想法,加上我也希望我的小孩能夠回臺灣接受一些臺灣的文化薰陶,就算他們之后念大學回美國,這能讓他們更具有國際觀的視野。那時候工研院有人問我有沒有興趣回臺灣工作,所以經過一些有趣的過程之後,我到工研院任職,所謂有趣的過程,主要還是因為有人對我的政治傾向有所疑慮,因為我在美國是臺灣同鄉會的會長,而且參加很多支持民主化的工作,主要是關心臺灣發生的事情並服務在美國的臺灣同鄉,大家偶爾聚會互通有無。這個同鄉會沒錢沒人,活動經費都要自己去想辦法,我回到臺灣也創立了幾個類似的協會,但都是與科技有關的活動為主,例如臺灣電子材料元件協會、臺灣智慧電網協會、臺灣產業科技推動協會及臺洋科學文明策進會等非營利組織,這些都是服務性的社團組織,也因為有這樣子的經驗,所以在前總統陳水扁先生競選期間,我也參與撰寫科技白皮書,這也促使我後來加入政府團隊,為國家及社會服務。
Q5.紀老師您曾經領導國內光電半導體最頂尖的團隊,請問您當初是在什麼機緣下組織這團隊呢?團隊是如何邁向成功之路的?
我在1990年回到台灣任職工研院,擔任材料所(後來整個組轉到光電所)組長一職,主要還是負責光電半導體元件的開發工作,當年在工研院材料所第一個主導的專案是開發AlGaInP 紅光雷射(LD)及高亮度發光二極體(LED),由於當時台灣尚無實際生產雷射二極體的技術,頂多是進行一些發表論文的研究工作,由於工研院的任務並非以基礎研究為主,而是要進行工業技術的開發,我把任職貝爾實驗室時期所累積的研究心得及儀器設備規劃的經驗應用到AlGaInP LD及LED生產技術開發,這期間最重要的兩件事就是決定以MOCVD磊晶機台取代LPE磊晶設備及研究人員的職責安排,因為我所要帶領的這些工程師從未做過這樣的工作,大多還是以工研院文化為核心的行事風格進行研發工作,所以研究人員的職責安排及心態調整,也極度關係到計劃的成敗,當然我要把貝爾實驗室的文化或管理方式落實到我所帶領的這個團隊也不是一蹴可幾,還是要經過一段磨合時期及執行方式的調整才可能達成目的。這計畫的成效可由當時的參與人員加入國聯光電的創立及稍後的晶元光電的成立可獲得證明,這計畫所開發出的相關技術的擴散是相當成功的,例如陳澤澎博士等人加入新創立的國聯光電,李秉傑及周明俊博士主導成立晶元光電,當然還有許多參與本計畫的人員一起加入到台灣相關的產業界。
Q6.為什麼會想到大學教書?
當我想從美國回來臺灣的時候,一開始是有想要到大學裡面教書,但我想說我在貝爾實驗室從事研究工作,從來沒有教過書,所以就想說可以先到工研院先做個幾年然後再轉到大學,在大學教書比較自由,沒有人會關切你該做什麼而不該做什麼。我會開始思考應該離開工研院去大學教書的這件事,主要還是政治的因素,1992年立法委員選舉的時候,因為我支持非國民黨的候選人而受到工研院高層的關切,我不太能夠適應這樣子的文化,所以在工研院任職4年之後,我選擇到中央大學物理系任教,那為什麼會到中央大學任教呢?主要是在此之前我就在那邊兼過課,那為什麼會去那邊兼課呢? 因為在此之前中央大學物理系有3個教授來找我,他們需要有製作radiation detector相關經驗的人,協助他們製作radiation detector array, 這是他們執行在歐洲粒子加速中心與丁肇中博士合作計畫所需要的東西,所以我就去那邊兼課教他們一些相關的知識及建立實驗室。因此當我有想要到大學教書的時候,自然馬上想到的就是中央大學物理系了。在中央大學物理系任職到2009年,之後轉到交大光電系任職到2013年退而不休,繼續留在學校幫忙國際合作事宜。
Q7.紀老師您退而不休,雖然沒有繼續做研究及教書,但仍然關心台灣社會發展,因此也沒有閒下來,能不談談你目前主要是從事哪些活動或參與哪些事務?
我在2000年被借調到行政院擔任研考會副主委負責政府的電子化工作,期間有關政府行政的無紙化、網路報稅系統、戶籍系統數位化、國家檔案局及國際物流業、電子商務等業務,是我在任期內努力爭取經費去實行。2004年轉任國科會副主委,建立了行政院的能源政策及科技指導小組並擔任第一任的執行秘書,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則是擔任召集人。我們推動很多能源政策的規劃及再生能源的落實藍圖。這些工作都讓我非常感恩有機會為臺灣的社會做出真正的貢獻,不是僅止於學院派的知識人對社會的人才培育及意見形成的努力而已。2008年回到學校,我就開始思考如何推動臺灣人心理建設方面的工作。到現在為止,我已經集結了近百位志同道合的各界人士,組成了臺灣科學文明啟蒙運動的推動組織,希望能提升社會大眾的獨立思考精神,落實科學精神的生活及批判思考的模式。讓臺灣不僅硬體設施還要在精神層次也進入現代化公民社會的境界。
Q8.紀老師您對現在的年輕人和我們學會有什麼建言和期許呢?
想當初我們出國留學是半年的薪水不吃不喝才能購買到一張到美國的單程機票,現在半個月吧,所以臺灣完全跟得上世界上已開發的國家經濟水平,雖然我們這一代有很努力打拼,而且年輕的一代有跟上來,造就今日的臺灣,真的很棒,所以我自己是覺得年輕的這一代要有自信心,因為台灣在各方面都不會比先進的國家差,學術研究方面都跟得上國際,所以要勇於發聲表達自己的看法,不管在國際上或者是自己的國家的各個領域。我要鼓勵年輕人不緊要努力賺取第一桶金,還要參與啟蒙運動,讓自己和臺灣社會進入真正人性化的生活美境。

圖一、(上圖) 紀國鐘教授與許進恭教授於2024年合影
(下圖) 紀國鐘教授與蘇炎坤教授及許進恭教授於2000年同遊舊金山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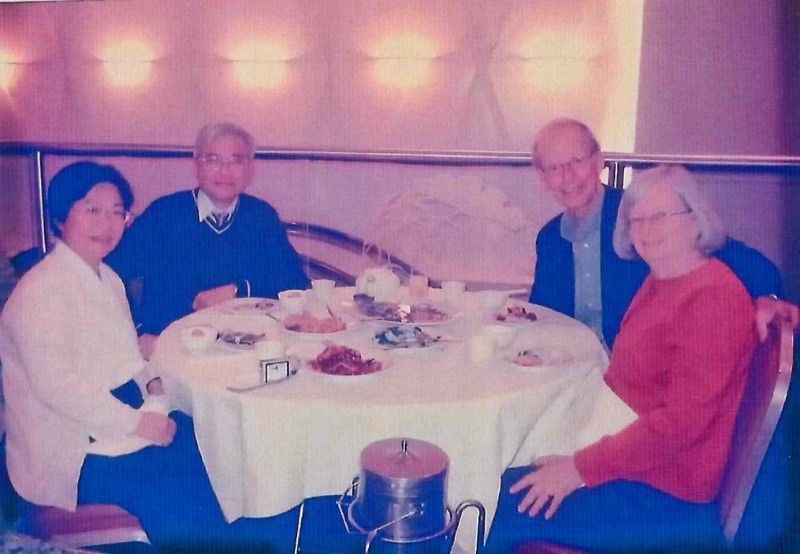
圖二、紀國鐘教授夫婦與紀國鐘教授之博士班指導教授合影

圖三、紀國鐘老師與交通大學光電工程系2012年畢業學生合影紀念
